从Moose Pass下来我们很快进入了一片雪松林,天边还残留着一抹红云,森林里却已经一片幽暗,伸手不见五指了,雪松一棵紧挨着一棵密不透风,地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枯黄的针叶和苔草。我们加快了脚步,奔着那稀疏的空地往前去,想逃离这突然袭来的黑暗,却很快发现前面无路可走了。
一入黑找路就成了件要命的事,树上的蓝色标记没有反光,一不留神就要走错路,要是碰到有巨石挡路,就更难做出明智的判断。好在有三个人,可以分头探路,谁第一个遇到蓝标,就把其他人唤过去,然后继续。也不知道我们到底纠结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迷途知返,总之速度越来越慢,脚下的路也越来越难了。
GPS表早就纷纷告罄了,我之前没打算要给手表充电,觉得用到什么时候打止都无所谓,反正剩下的距离也不多了,也许其他人也这么想。根据先前的计数和之后走的距离估算,眼下我们应该已经早就结束Threenarrows段,进入了路况最容易的Baie Fine区。

Evening Silhouette (1926)—Arthur Lismer
出发前船长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距离图,上面标着所有营地之间点对点的距离(一路上可以根据树标确认营地序号),可似乎没人把它放在心上。等想起这回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状况不大好:我跟火娃的图都湿透了,杨磊压根就忘了带。可这样盲目地闷头走实在不是办法,最后我们把最有希望的火娃图拿了出来,三盏满怀希望的头灯屏气凝神地聚焦在一处,然后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慢慢揭开,火娃图很争气地保持了完整之身,然而最后一揭宣告了一切的终结,上头的字已经全洇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火娃拿出手机上的离线地图,开始一段一段地作加法,“2.4加0.8加0.8加3加……”他一直加,最后加出来还有至少16公里,什么呀?那等于现在连Threenarrows都没走完,我一下子沮丧之极。
北美的超马赛总爱在距离上戏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官方距离总跟我的GPS表数据有出入,可明明我的表训练的时候一贯很准的呀。有的比赛会耍前长后短的把戏,最后的总距离差不多,选手们大概也不会计较,有的比赛干脆比书面里程超出一大截,选手们也无可奈何,完了赛反而有些得意,你看我其实都不止跑了一百迈。有一回我都已经是争分夺秒的节奏了,他们跟我说离下个河边的补给站只有四公里,结果我都跑了超过八公里,河水还不见踪影。我总在内心不停呼唤那些补给站的名字,Bonnivier,Cayuse Flats,Lac Cascapedia,你们在哪?你们到底在哪啊?
时间在一点点地延后,我们越来越慢了,之前火娃还纠结夜里十二点前到了营地,洗完澡到底是先热煲仔饭还是先煮越南粉,后来又说要是半夜到,就干脆先去湖边坐一会儿等天亮,免得吵扰到营地,直到最后我们都明白,天亮之前是注定到不了了。
我们走过一条扛船道(portage, 专为canoe camping设计的湖与湖之间衔接的中转道),火娃说,你知道吗?这是一条portage,居然还有这么长的portage,我沉默,一言不发。三个月前船长和火娃专门来探路,回来后他们两个一致说最后三分之一(大概有超过20公里)十分跑得起来。可眼下我们正走过一条涨水的乱石滩,支离破碎的溪流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头,别说跑,根本连下脚都难。我们离出口越来越近了,却从来没有一段平坦的路能连续超过两百米,不知道到底哪只眼睛看出来最后这部分是跑得起来的。“最后三公里会很好跑”火娃反复强调,可最后三公里在哪?
在火娃的喋喋不休中,我感觉自己的耐心终于被消耗得差不多了,那些过往力不从心的懊恼劲儿也从心底里一股脑地涌了上来。夜更深了,越来越多的路标难题在前方等待我们去解答,有时候我们集体犯迷糊,竟然连来时的路都不确定了,不会又走回去了吧?好在三人团队的纠错能力不容小觑,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火娃倒没有很低落,显然他已经接受了天亮才能走出去的事实。三个月前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正值仲夏,暴雨倾盆,飞蚊遍地,他身上被咬了上百个包还得背大包与四处流淌的烂泥搏斗,与那时候相比,眼下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太糟。
杨磊还在与睡魔搏斗,有时候我们停下来找路,他一坐下就低头昏睡过去,但几秒钟后又迅速惊醒过来。为了提神,他常常主动走在最前面领路,但很快我们又会发现不知身在何处了。于是我们轮流在前面走,永远警醒,永远纠错,循着一个树标走向另一个树标。
火娃还在不停地算加法,有时候我们已经都走出好远了,他报出来的数字还跟一个小时前一模一样,甚至还更多了。我烦死了,实在一个字都不想听了。可除了他的运算结果,我还能靠什么来了解当下处境呢?我心里恼怒,可又不知道这恼怒该冲着谁。冲火娃吗?他之前也只走过一次,总不能苛求他对这路上的一切都过目不忘。冲这路?全是我们自己要来的。船长?人家专门准备了详细的后备数据,是我们不把他的提醒当回事。是我自己总不想事先了解太多细节,什么准备也不做,可事到临头又难以忍受这一切带来的茫然无措。其实终归是恼怒自己,在山的巨大和大自然的广漠面前,总是如此地不堪一击。
我的眼前是一片片呼吸缓慢的积水/月亮苍白地挂在水上/古老的黑暗浮上来/山丘以及鹿的眼睛/它们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
我一直忘不了意大利奥斯塔山谷里的那个夜晚,那时我正经过小镇中心要回住的旅馆,路上空无一人,我独自穿过街道,下到一片开阔的山间空地上。一轮明月冷清地挂在高空,月光下远处的大天堂峰(Gran Paradiso)静静地伫立着,此时我站在一条由织毯铺就的长廊上,头顶是一个红色的拱门。两天前的清晨我正是从那里出发的,那时的我忐忑,兴奋,对即将开始的旅程充满期待。
然而两天一夜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的膝盖已经痛得不行,我的嘴里已经长满了口疮,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垮掉了,好不容易才捱到了接下来的补给站。那时比赛正进行着,很多人还在补给站里整装待发,有人劝我继续,可剩下的路那么漫长,终点还遥不可及。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退赛了,当时我一心只想从难以忍受的痛苦里获得解脱,一刻也不想耽搁。
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出发的小镇,赛事中心值班的热心姑娘把我送到了旅馆门口,她很友好,一路上跟我聊东聊西,“可你看起来很好呀”临走时她终究有些疑惑。空房当然是有的,大部分人都还在山上,旅馆主人几乎不懂英语,得靠翻译软件勉强交流,但他们很照顾我,提着行李送我上楼,体贴地帮我带上房门。
门一关上我就开始流泪,胖胖在罗马玩得不亦乐乎,他巴不得我早点离开这儿去跟他会合,可我根本不想去那里,这时候我原本该在山上。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我一直期待的旅程,那些我还未曾遇见的山,眼下只有空洞的身体,无力收拾的脏乱行李和无法挽回的刺眼败局。事到如今,没有人可以安慰我,我趴在旅馆房间里恸哭,没有人能听到。
此刻我又站在了大天堂峰下,一路上我曾无数次地凝望过它,它那么美,在脆弱无力的时候总能给人以安慰。我记得坐在Col Loson垭口一直放声歌唱的人们,记得爬山路上几个轻托着我的包,围着我跳舞给我加油的小伙子,记得山原上那两头打架打得如痴如醉,险些撞到我身上的淘气小毛驴。如今在山下回想这一切,我只感到凄凉,非常凄凉。我多希望自己可以展翅高飞,重新回到那高山之巅上去。可现在我的翅膀折断了,凋落了,僵死了,我的身体被掏空了,哪里也去不了了。一根刺从我脚趾上,手指上,从我的头发根,从我身上的每一处毛孔里扎进来,一直扎到我的最深处,对此我无力抗拒,我连把它拔掉的力气也没有,这痛苦远甚于退赛时身体所承受的痛苦。
我在那里站了多久呢?一小时?两小时?还是更长?一切都结束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催促我做任何事了,我站在夜空下,任凭那些后悔痛苦自责在心底里翻滚,它们像潮汐一样无休无止地涌上来,而我面前那座巨大的雪山一直静默着,岿然不动。有一刻我好像突然感觉到了一种目光,是山在看我的目光。它看着我出发,看着渺小的我在那个巨大的天地间爬上爬下。它看着我走自己的路。它目睹着我的不安分,目睹着我的忍耐,目睹着我的挣扎和脆弱,也目睹着我的苦痛。这目光让我感觉到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安慰,一个可怜的安慰。
我回到旅馆,离开时一片狼藉的房间已经被主人收拾得整整齐齐,我倒在床上又昏睡了过去。第二天大清早我就起床了,我收拾好行李,搭上了去往佛罗伦萨的大巴,傍晚的时候,绯色夕阳下的米开朗基罗广场上又多了一个东张西望的游客。
—
“还记得那条河吗/她那么会拐弯/用小树叶遮住眼睛/然后,不发一言/我们走了好久/却没问清她从哪里来/最后,只发现/有一盏可爱的小灯/在河里悄悄洗澡”
夜已经很深了,星星散开来,包围在巨大的树林上空。
先前我们在路上走,杨磊说好像看到了灯,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两盏亮咚咚的小黄灯,我想我已经猜到了那是什么,后来我们果然在不远处的树丛里,又看到另一头很健美的白尾鹿。
我在森林里看见过各种各样的灯,黄色的灯,绿色的灯,蓝色的灯,草丛里的灯,山腰上的灯,一动不动的灯,边走边晃的灯,一眨一眨的灯。我也听见过各种各样的声音,草丛里悉悉索索的声音,咚咚踩水的声音,入水时的巨大水花声。有一次我甚至还听到了杀戮的声音,从不知什么地方猛然暴出来的一声尖叫,越来越凄厉然后渐渐衰弱,直到一切重归宁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时候我会停下来一小会儿,关掉头灯,什么也不想,只为了听一听森林深处那些悄无声息的运动。可如果是比赛,恐怕连这也成了一种奢侈,只要有那面步步紧逼的计时钟,在赛道上我们就不得不在急驰,在逼迫,在挣扎,在焦躁贪婪地追寻,在不停地对自己说好多自欺欺人的话,就像身处现实。
而此刻我们并不在赛道上,不再有补给站、路标、成绩和关门时间,也不再有任何规则,终点可以忘记,时钟也可以停止,我们就这样全然地置身在密林的最深处,靠着我们身上还未泯灭的对自然的某种感应,在缓慢前行中,捕捉着黑夜森林山岳星辰的隐秘故事。

original shot by Yi Wang
树林深处传来猫头鹰的怪叫,“Who-cooks-for-you? Who-cooks-for-you-all?”我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超想念营地里热腾腾的越南粉,可它还远在黑夜的另一端。像样一点的东西都已经消灭完毕,实在不想再逼自己吃那些甜得发腻的胶和棒了。“Who-cooks-for-you? Who-cooks-for-you-all?”更远处有另一只猫头鹰在跟先前那只一唱一和,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啃起了牛肉干。
我终于想起来前几天船长在活动群里发过一张距离图的截图,我打开手机,欣慰地发现眼下想知道的数据正好都在截图范围里。火娃累加的结果大致是对的,走了这么久,我们剩下的路仍然很长。当然是有些失望,但这也远好过一直埋头瞎走。再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所有人都不怎么说话了,只是继续往前。
过去的一整年我跑步都很少,我本来就很难安分守纪地训练,又不喜欢被目的感束缚,多伦多离哪里的山都远,周边的越野道跑来跑去全是那几条,经历过那许多微妙特别的时刻,紧挨着城市的日常重复渐渐很难让人提起兴趣了。上个冬天我们迷上了越野滑雪,那是另一个世界,在雪地里风驰电掣的感觉棒极了,跑步愈发被抛到脑后了。
我爱高山,爱全然的荒野,爱那种彻底远离尘世在深处游荡的感觉,东跑西跑地参加了好几年的超马赛,我生命里一下子多了很多关于山关于森林的故事,但无论是赛前还是赛后,却再难有当初的那些激越战栗了。可这也没什么不好,比赛未必要全然地追求突破极限,在哪里跌倒了也未必要在哪里爬起来,故事的好坏不该由字面的结果来定义,也许只有当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才能看到山、森林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样子。
一路上火娃一直在我身后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他到底在念些什么。火娃大致不怎么靠谱,但在一头雾水时他总是最有信心做出判断,尽管常常冠之以前缀“我感觉”,“我猜想”以及“我预测”。杨磊说自己相信他,至少三个月前的徒步无助于记忆也该有助于直觉,我所见略同,于是我们就靠着火娃的直觉以及分头行动,一路摸索过来,竟也渐渐越来越了解这些树上记号背后的隐藏逻辑。
“哎,你开始是说最后三公里很好跑是吗?”看来杨磊仍然心存希望。
“我不知道”。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抵达了最后一个河狸坝,火娃好像着了魔,兴奋地冲过去,一边惊叹河狸工程的规模巨大,一边在断木上踩踩跳跳。再抬起头来,他已经跳下来,在和坝底一丛韧性十足的乱草搏斗开了,也许他是想从下面绕道走。杨磊拄着杖一步一探地从坝上头走过去了,他把杖递回来,我们也借着它挨个过了河。河狸在此地的筑作大概有几十米长,泥坝上横七竖八一大堆断树石块残枝烂叶以及各种各样腐朽的东西,但看起来也坚固得很,很难想象这一切是仅凭一狸之力,也许是几个家族合力的成果也说不定。

The Beaver Dam(1919)—J.E.H. Macdonald
—
过了河狸坝,路终于平坦起来,乱石树根勉强在此止了步。杨磊匆匆地往前去了,他开始急着要结束这一切,一整夜的困意把他折磨坏了。他飞快地跑了起来,很快不见踪影。而我却一步也不想再跑了。
天色渐渐发白了,我们身旁的一方湖面现出身来,阳光还未显露,湖面上没有一丝亮光和色泽,然而这是她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静得让人能听见她的叹息。我记得所有那些日出前我曾跑过的湖,Macdonald Lake,Nicomen Lake,Lac Gouache,它们总是在漫长的黑夜之后不经意地出现,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让我获得某些力量,就像恩典。

Night Pine Island (1921)—Alexander Young Jackson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又渐渐跑得多了起来,火娃老早就千方百计地想要跑长距离为La Cloche练兵,久荣从七月开始了自己的Bruce Trail End to End周末计划(位于安省尼亚加拉断层带上全长超过890公里的长径),最近我们也都跟着去凑热闹。我们跑过一片片的野苹果树,跑过幽暗密翳的山谷,跑过空无一人的滑雪场。在空旷的原野上,夏天被疯长的野草和起伏荡漾的麦田一分为二,一直涌向看不到边的尽头。有只小狗遇见我们时兴奋得不得了,一定要往每个人身上扑好几下。我们往前走了好远,它竟然又追来了,一直冲到最前面,执意要当我们的领跑。主人气喘吁吁地追来了,我们停下来,最后它被主人紧抱着怔怔地看我们走远,它多想尽情地跑一跑呀。

在Seaton Trail上我认出春天里有过一面之缘的Tom和他的两个黑家伙,总是走在前面的是四岁的Habova,安静地挨着Tom的是七岁的Samantha,Tom不相信我还留着半年前拍下的三人行合影,于是我又拍了另一张。告别Tom之后,我陷入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欣喜里,竟出神地在其中的一小段来回瞎跑,怎么又跑回来了,遇见了我好几次的一个家伙大声地嘲笑我,可明明是被他的另辟蹊径误导了呀。我的手心沾满了汗水和Samantha温柔的唾液,头顶上一只啄木鸟正趴在那咚咚咚地瞎忙活,我渐渐觉得自己好像终于可以重拾跑步的意趣,不管怎样,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啊。

新的一天终于来临了,一切都开始分明起来,长满青草的斜坡,远处层层叠叠的花岗岩,蓝色的树标不再像黑夜里那样模拟两可,它们重新兢兢业业地履行起了自己的职责,给予我们引导与鼓舞。森林里霎时间又活跃起来,鸟儿歌唱,蛰虫鸣叫,一只机灵的花栗鼠从我们面前飞快地跑了过去。我们离出口已经很近了,虽然疼痛还在,但脚步又轻快起来了。
于是我们出了山道,走过乔治湖上的最后一座小桥,晴朗的日子里乔治湖显得格外亲切,它友好地敞开心扉,仿佛一直守在那里对我们翘首以待。在那里等待已久的还有胖胖和阿里山姑娘,胖胖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先头部队出山道时的景况,阿里山牵着火娃的手,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上,阳光在微风中轻轻流转,最后停落在他们的背影上。我也在阳光里,我呼吸着湖面上的蓝空气,几乎要忘了刚刚在深处发生过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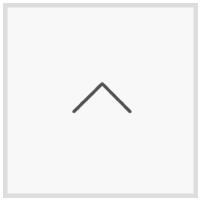

回应
回应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