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战斗,2014 澳大利亚The North Face 100 Blue Mountains
蓝山,我的首个百公里。
14个月之前,我坐在counselling的诊室里,告诉咨询师我有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的迹象。他说“试试跑步吧!”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两个月后,第一个半程马拉松;五个月后,第一个全程马拉松;八个月后,第二个全程马拉松跑进四个小时。堪培拉建都百年,第一次尝试30km越野,600多米爬升跑了近3.5小时;然后在某人的怂恿下中抢到了2014年澳大利亚The North Face 100的名额。很奇怪的是,从去年12月报上名之后,一直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行性问题,虽然100km在正常人看来是一个想象之外的距离。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性格中有太多莽撞和不稳定的成份,天生的risk taker,时刻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让自己保持兴奋状态,设定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目标,从来不肯说“某某事这辈子我都不敢想也做不到。”跳得高摔得惨,然后爬起来继续折腾。

澳大利亚 The North Face 100在2014年刚刚加入Ultra-Trail World Tour阵营,总爬升4100米,在 UTWT的十大赛事中属于入门级别。赛事总监Tom Landon-Smith 说“我本意不想让选手受罪,只是尽力让他们享受澳洲森林的美好。”8过,难度这东西是相对的。说个好笑的,赛前Briefing的时候Tom告诉我们,2011年Kilian Jornet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Who are you?”,赛后感想是赛道“Fast and flat”, 自然台阶特别多是一大特色。对于Kilian等精英跑者来说4100米的爬升未免太过缺乏挑战,对于我等新手还是足以虐得灵魂出窍,欲哭无泪的。
不管再怎么不靠谱,我还没有甩到去裸跑一个100km。去年10月的墨尔本马拉松之后,逐渐切换到跑山模式-堪培拉以bush capital著称,开门见山-于是每日回家之前上下Black Mountain10km成了习惯。后来加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越野跑俱乐部,第一次发现天份和努力的积攒都不够是什么状况,每周训练拖在一群健硕的本地青年队列末尾,拼到吐血都很难跟得上;断断续续参加本地的越野赛,距离在30km上下,无一例外地混在末尾20%,和中老年组混在一起。半年以来,遇见很多优秀的本地跑者,肌肉纤长,身材像猎豹,半程山地比我快30分钟以上,比较之下觉得自己特别笨拙而不堪,在一段时间内深陷自我怀疑的死循环。然后到了三月,四月,复活节假期专程去蓝山的赛道实战演练;之后一个星期,踩着生理期撑完了Mt Solitary Ultra 45km作为练习赛。Mt Solitary Ultra的赛道与TNF赛道部分重合,难度甚于TNF100,7个多小时的完赛时间多少给了我一些信心。
现在澳大利亚 The North Face 100已经过去一周了,翻看澳洲精英跑者Brendan Davies的报告不禁眼眶发热“…这么多人,他们奔跑,行走,跛行,或者磕绊着,甚至爬过难以想象的漫长距离,只是为了感受越野跑运动的魅力,接近每个人的宏大目标。赛前几个月无休止的长距离、山地、蓝山实训-汇集为大战前夜的焦灼以及自我怀疑…分头作战, 在奔跑中承受痛苦,抵达我们从未想像过的深度,然后在终点相会,在一切的一切结束之后,为彼此的喜悦与成就举杯相庆…”
是的,就算是在泥里爬行都值得回味,只是我错过了终点,错过了结束的喜悦。

大蓝山地区是列入UNESCO名录的世界遗产。在Gundungurra人创世纪的故事中,半鱼半蜥蜴状的史前巨兽殊死相搏,将高原台地撕开深长的裂口。如今,山崖峭壁与深谷交错-山脊覆盖尤加利树与石楠,峡谷深可达800米,雨林遮天蔽日,若非岩降无法进入。天气晴好之时,尤加利树香脂混合水汽使群山泛起通透的蓝——不只是蓝山,尤加利树成林的地方空气里都弥散着这样的蓝。
22000年之前,蓝山是Gundungurra人的国家。在这片大陆被发现之前,它是数百个语言系统与文化传统各异的国家。如今,The North Face 100在蓝山地区举办必须要经过Gundungurra部族的许可,而大战前夜由Gundungurra长者Aunty Mary King向跑者致辞-“欢迎来到这个国家(不是澳大利亚哦,这里指的是Gundungurra领地)”-也是多年来的习俗。
今年老太太身体欠佳便由她的儿子 David King代劳。他慵懒地环视我们一眼,露出狡黠的笑容:“晚上好啊,真高兴看到这么多的笑脸。我最喜欢大战前夜,每个人看起来都斗志昂扬-你们签署了免责声明,表示自己充分理解 The North Face 100是什么,你们宣称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超越自我、享受大自然。好吧,明天我会领着一帮人在38km处的树林里吹吹打打,到时候你们再告诉我自己在做什么-但愿那时我看到的不是白眼…”
好吧,好吧!我承认在很多个时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踏上赛道;在很多个时刻,自动照相机捕捉到的影像都仿佛是癌症晚期患者,但至少那不是在38km处。

回想起来,一切的开始还是愉快的。一个完美的五月的初冬的早晨,6:30来到起点的时候,第一组起跑的选手已经出发了。 The North Face 100 Australia 根据选手的既往经验分区出发,避免赛道上出现拥堵。没有任何越野跑经验的我,被分在第6组预计在19小时-28小时之间完赛),6:50起跑,落后精英跑者20分钟-可是雄心勃勃的我居然琢磨着在20小时内完赛。为什么是20小时呢?因为苛刻的The North Face 100 Australia 奖励排名前三的男女选手金腰带扣,14小时以下银扣,20小时以下铜扣-多于20小时啥都木有。跑进20小时加入澳洲超马跑者俱乐部,俨然咸鱼翻身成为“ultra runner”,顿时高端大气起来,土鸡变凤凰。而后面的故事充分应验了什么叫跳得高摔得惨。
按照事先约好的,与小明同学在起点处碰头,我们将在这一路上结伴同行。早在2012年就知道小明了-严冬冬在天山遇难那一年。小明在国内登山圈子很活跃,作为严冬冬的学弟他们有过一面之缘,那年他的缅怀文《魂归天国,自由长存》在人人网被广泛转载。2012我还与“自由”二字牵扯不清,对精神层面的纯粹有着死死的执念。后来才逐渐明白人生而不自由,但是有那么一些事物可以使你产生自由的幻觉-比如越野跑,比如登山-不知不觉被幻觉支配、淹没,觉得自己握住了求生的稻草。2013年,我们在墨尔本马拉松相遇,当时他刚刚登陆澳洲一周,都是巧合。对于雪山经验丰富,对于越野跑却和我一样是新手,两个人,傻傻地去冲击20小时的完赛目标。

CP2之前,无比顺畅,几乎无任何不适感。开始的4公里沿Cliff Drive折返跑且当是预热,迎面闪现过无数熟悉的面孔:越野跑俱乐部的Tom, 自信满满直奔14小时银扣而去;多次定向越野的搭档Craig,头裹新西兰国旗,跑在50km队伍的前列;Mt Solitary Ultra遇见的小个子日本人,穿运动bra有四块腹肌的祖母级跑友…微笑点头,绝尘而去踏上各自的征途。
沿Furber Steps向下进入Jamison Valley, 这段赛道再熟悉不过了,复活节训练跑过,Mt Solitary Ultra跑过。但是在两个地方造成了拥堵,一个是Lands Slides,另一个是所谓的“恐怖阶梯”-一段垂直的金属梯,其实一点都不恐怖。骑行过川藏线的见过大堵车不?对对!就是那个意思!窝心,心里着急,嘴上却与小明彼此互相安慰时间还充足。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按17小时完赛的配速奔跑,比预计时间提前30分钟到达CP1。
之后是平整的防火道,风光宜人,两旁丛林里埋伏着辛勤工作的摄影师,趁各位跑者状态尚好诱导我们摆出各种很high的造型。我们前面四位本地鸡血青年手牵手跳起来了!于是我们也跳!与几个小时之后的垂死状形成了鲜明对照(赛后这些照片将以30刀一张,80刀全套的价格出售,暴利哈!)

CP4之前每一段的间距都比较短,我清空了水囊,保持轻装,前置的水壶维持500ml Endura,在每个CP点之前喝完然后装满,一路高速前进,我们渐渐赶上了第五组出发的选手。即将抵达CP2之前,小明的右腿开始严重抽筋。我扶他坐下,放平小腿,放松肌肉,轻轻加压按摩。大概10分钟之后他终于可以勉强站起来行走了。CP2前的最后1公里,我看得出他强忍疼痛在坚持。到CP2比预计提前了1.5小时,这样的小点原计划速度掠过,可是我们停留了15分钟让小明得到充分修整。

出CP2经过山谷中的牧场,弥散着马粪和青草气息。接下来一段陡直的爬升,David King与他的伙计们就在转角等我们啦,嘴上挂着戏谑的笑看我们大汗淋漓地挣扎-38km到啦!是的,Aunty Mary King年轻的时候,腰间裹着块负鼠皮光着脚丫跑遍了蓝山危机四伏的角落-对于他们来说,奔跑就是本能,到了我们这里何以被渲染出如此多的英雄主义悲情呢?想想真是矫情!在他面前不想表现出痛苦狼狈,强打精神还能笑得出来。
之后是陡降-右膝盖外侧开始刺痛-试着触摸、按压,韧带还是完整的,压痛点局限在外侧,略松一口气,心知髂胫束综合症找我来了!跑步以来一直注意防范伤病,左踝2008年徒步船底顶得时候落下旧伤,而膝盖从来没出过状况。髂胫束综合症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极其讨厌,一到下降地形就开始抬头,慢性疼痛反应惹得情绪极差。从这里开始,我最有优势的下坡不得不荒废了。
我们比预计时间提前2小时抵达CP3,这也是开跑后第一次见到我亲爱的Support Crew-我老公。按事先约好的,他带来了两瓶含糖冰可乐!高糖+咖啡因在平时是毒药,在此刻却是救命药!疼痛在心理上引起的反应被压下去了。但是过度自负的我作出了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请求老公去帮我找一盒Panadol-Nurofen我知道经常会引起肠胃的麻烦,而Panadol平时痛经或者偏头痛都会时不时来上几片的。不曾料想,在体力耗竭与夜间低温的状况下,小小的药片直接导致我退赛。

此时是第46km,下一个补给点CP4在Katoomba镇上的室内体育馆,距离区区11公里,可以到那里再大吃一顿。陡升的血糖和咖啡因作用让我处在极度兴奋状态,恨不得立刻出发。但是小明的脚上打了疱,已经脱了鞋袜休息,不得不又耗上20分钟。
“Hi!又见面啦!”离开CP3之前小个子澳籍日本人Hideaki刚刚到达-身材比我还娇小-我们在Mt Solitary Ultra的赛事中相遇,曾经有过长达20km的“厮杀”-那次我凭借神一般的下坡速度在最后领先他15分钟完赛。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与我们不同,他虽然在前半程落后,但从不在任何一个补给点停留过久,始终维持奔跑的状态,所以我们离开CP3是同步的。
这也是Hideaki的首百,同样是20小时以下的完赛目标,Mt Solitary Ultra也是他的练习赛。
“我去年4月悉尼海岸长跑节跑了第一个半程,你呢?”“我是在堪培拉马拉松,差不多时间吧!”
“我中间有十多年没跑步了,之前在日本还是很活跃的!”“好吧,我来澳洲才开始养成运动习惯!”
“46km是我练习过的最长距离了,之后都是未知啦!”“我也是!”
我嘴上嘻嘻哈哈地乱侃,心里却憋着劲-上次带着大姨妈都跑赢你了,这次怎么能差呀?!而且,而且我最不愿意输给日本人了! CP3-CP4是蓝山著名徒步路线Six Foot Track的一段,主要以缓缓起伏的防火道为主,最后是Nellies Glen的900级台阶700米爬升,髂胫束综合症影响不大。因为一路死死咬住Hideaki, 这一段速度明显提上去了,再度回头的时候小明同学已经不见了。后来在看到他发了一条充满怨念的微博“54公里,肠胃翻滚,好样的,该来的都来了。一个人战斗!”是不是在抱怨搭档被日本人拐跑了?真的不是!我在和鬼子较劲呢!自己人“战斗”个什么呀?
去年我的一个学生在赛后评价道:“I still don't know who Nellie is but I learnt to hate her in TNF。”他是一个澳洲本土肌肉男,足以见得Nellies Glen的台阶在这样一个午后,54km的疲劳之后是多么丧心病狂!可是因为身后有一个Hideaki,我状态神勇,居然期间没有停下来休息,900级台阶,一气呵成。最终我与Hideaki前后脚进CP4。

位于57km处的CP4是大赛分水岭, 整个TNF100 Australia的赛程是环绕Jamison Valley的两个环路。先由 Furber Steps下到谷底,再经Nellies Glen爬升回Katoomba小镇,这才是第一个环路,也就是整个白天的奔跑路线; 过了CP4,沿Cliff Top Walk 反向奔跑,经过无数无数的台阶和骤降的防火道降至Kedumba Valley,最后再经过惨烈的爬升回到峭壁顶上去!——我觉得今年赛事最惨无人道之处就是最后10km全部是令人发指的剧烈爬升!过了CP4比赛才刚刚开始,这个补给点设在镇上的用意估计是:嘿!菜鸟们!前方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该退就退罢!
对于我们这些后50%的选手来说过了CP4便是黑夜。赛事总监Tom说,对于速度够快的精英跑者来说,夜间的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夜幕的降临对于他们意味着战斗结束。而对于普通人,任何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都可以成为致命的问题。从这里开始,我们必须换上足够的保暖衣物,夜间反光背心,携带抓绒上衣和防水裤。强制装备中甚至还有固体酒精和防风火柴-如果深陷窘境至少可以裹在救生毯里面生一堆火避免被冻死。这都不是玩笑话,赛前精英跑者论坛上Brendan Davies介绍他的首百就是以裹在救生毯里等待搜救队结束的-他是唯一一个坦诚糗事的牛人,很shy但很真实,TNF之后我对他好感骤增。
”Pain is whatever the experiencing person says it is, existing whenever he says it does!”疼痛,多半是一种情绪上的主观感受。有时它提示肉体的伤病,更多时候只是无谓地消磨意志,让人脆弱而矫情。
比赛前夜,看过一篇本地跑友的经验帖谈道当疼痛来袭萌生退意之时,依次尝试:水、糖、电解质、咖啡因-总有一两样会起作用。如果全都无效,那么弄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任何空泛的抱怨和矫情都是无效的。我擅自在这个清单上加上Panadol。战意正酣的时候,实在不想让一条处于激惹状态的韧带影响发挥-我知道它没事,只是对奔跑的负荷不满打算罢工。
水、糖、电解质、咖啡因之后,吞下两粒Panadol,整装待发。这时,小明姗姗来迟。我瞥见Hideaki速度换装之后已经离开了CP4,也急于跟上去。Hideaki一直独自作战,他的妻子并没有来到赛场,也省掉了很多互诉衷肠的腻歪时间。
最后得知他的首百跑了19:40!强大的执行力令人叹服。
“怎么办?我跑不进20小时了!”此时小明被疲劳和疼痛折磨得很苍白.我让老公也分给他两粒Panadol,外加一大块炸鸡。好吧,这就是我对于痛苦的态度-有药吃药,一起哭没有用啊!
Good luck! 我的伙伴,我只能帮到这里了!为了目标我们只能分头战斗!

离开CP4的时候刚过5:00,天光尚明。就是说如果我能在9小时50分内搞定43公里,铜扣到手!我自信满满地告诉老公,我将在8:30-9:00之间到达位于Queen Victoria Hospital的CP5。
对症下药没错,怕就怕吃错药!噩梦般的旅程开始了…
Panadol的效果半小时后显现,一直以来唧唧歪歪的膝盖终于闭嘴了。之后的10公里跑得飞快,若干蹒跚而行的猛男看见我一路狂奔超越,不可思议地叫道“WOO! WOO! Good effort!”可是不对呀!身体变得很热,然后开始大量流汗,比正午强烈的阳光下出汗还要多-能量和热量随着这些汗液缓缓流失…后来得知小明在这一段也有异乎寻常的爆发。
Panadol并非灵丹妙药,它在中国有个很土的名字“扑热息痛”-对症效果很好,副作用也明显,比如肝毒性。虽然曾经多次服用这个药物,却从来没有在超马和夜间低温的极端环境中使用过,这次来了个副作用集中爆发:上消化道出血和失温。后来查阅文献,失温这一点比较少见,一般发生于体温调控能力差的儿童。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在某时某刻药物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奇妙的反应。
一个人的良药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一点没有错!
66公里, Giant Stair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头的金属台阶上,我猛然感到虚脱-危险的迹象,机械地补水、吃胶,凉水灌进胃里吸气都有刺痛感,脚步却不肯放缓。3个小时之后,疼痛开始以更迅猛的势头反扑,无休止上上下下的台阶仿佛酷刑,速度越来越慢,但是慢跑也总是会比走快,而走会比爬快,而就算是爬也快过止步不前!后来根据赛道上自动照相机显示,当时的状态完全就像一个癌症晚期患者。

“Hi!你好!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啊!”快要死的状态,突然听见这么一句没有没脑的话。 我抬起头, 一个高挑英俊的澳洲男生与我擦肩而过。满眼繁星璀璨,月亮还未升起来,借着星光远处金色的山崖绝壁若隐若现。
“是呀!天气真好!我一直在想抓绒和防水裤真是多余!”(是的!要知道2个小时之后开始失温你还会这么说吗?)
“从前参加过100km吗?” “第一次呢!”
“第一次能到这里已经很厉害啦!你知道吗能跑完100km你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不只第一次听见这句话了,可是我想说,越野跑这件事与生命的其他层面真的有联系吗?
男生叫Geoff,对于20小时完赛铜扣有着同样的执念,但是我们都那么不擅长台阶,都无法提速,我们都压在能或不能20小时完赛的边缘,Geoff一路絮絮叨叨给我洗脑。在半梦半醒的状态,20小时这个数字和2:50分这个时间牢牢占据了我的脑子。或许执念早点放弃了也不会有之后的煎熬。
渐渐地,台阶变成了平整的公路。“Sophie!你想不想进20小时。”
“想!”我已经气弱游丝了。
“我们跑吧!前面就是CP5了。Sophie,你听好,我不会在CP5停留很久。我们还有4小时50分去搞定剩下的22公里,将近5小时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很简单的。我出站的时候,记得跟住我!”
我麻木地跑起来,腿部僵硬,跑姿一定很难看。事后我老公说“你进站的表情仿佛受了惊吓。”
在CP5,腹部绞痛,去了厕所发现黑便 (有可能喝多了黑咖啡,当然事后分析也有可能是上消化道出血),之后一阵一阵恶寒。本不打算拿出来的抓绒必须穿上了,还是冷,颤栗到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试图跟随Geoff出站,但是颤抖得不能行走,Geoff失望地独自离开。坐在温暖的火堆旁边,老公紧紧搂住我,焦虑地问要不要找First Aid看一看。我拼命摇头,我知道一进那个医疗帐篷可能就此倒下止步不前。
Panadol的副作用已经显现,不可能用更多的药物去压制疼痛,这样的疼在生命的很多阶段无法回避。
“必须走了!已经在这里耗了15分钟了!不走实在来不及了!”
“烂猫!不要想那个20小时行不行!”
“不行!不行!”我从他温暖得怀里挣脱,跑进无边的黑暗之中。
“我在终点等你!凌晨2点之前!”我的老公,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从不跑步,但是会出现在我奔跑过的的每一个山头-从复活节训练,到Mt Solitary Ultra, 到今天The North Face 100的残酷挑战。
CP5的出站口一侧,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抱住她爸爸的腿不让离开。
我机械地迈动双腿,拼命忍住眼泪。为什么要奔跑呀?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自我折磨并让亲近的人在黑暗中焦灼等待?我不明白呀!
当我在那张免责声明上签下名字的时候,我真的理解了它的意义吗?我真的理解The North Face 100是什么吗?我真的准备好去承受失温、极度疲劳、滑坠以及随之带来的伤害以及-死亡?!-其实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想起严冬冬遇难前的那份免责声明,心里全是苦的。
从Queen Victoria Hospital出发的22公里,前后跑过两次,先陡降再陡升。记得三周前的Mt Solitary Ultra我风卷残云般从山顶狂飙而下30分钟内到底。此刻扑天盖地的疼痛却像一把铁钳压住了我的速度。颤抖依然在继续,伴随着强烈的腹痛。降至谷底耗时1.5小时,谷底是浅浅的Jamison Creek,这大约是第85km,Mt Solitary Ultra的时候,我们都图省事穿着鞋趟水而过-而现在赛事主办方在溪水里放置了平整的踏脚石-夜晚趟水极其容易失温。过河其实并不困难,可是…我的平衡感消失了,一脚踏进水里,彻骨冰冷。然后开始爬缓坡,步态变的更加不稳,黑暗中仿佛有一股股热风吹来。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失温了,却挣扎着不想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结局。
赛事医疗车徐徐驶过,有人探头问我一切是否安好,我硬撑着说没事,于是他们奔91km处的医疗救助点而去了。
心里很乱,The North Face 100之前的一个月,我连续经历了两场葬礼。4月初,系里的教授,在定向越野赛之前打过招呼,之后6个小时他在一道偏僻的山脊上心脏病发去世,救援队用了5个小时才赶到;4月末,曾经一起参加中国国家地理夏令营的90后男生急性白血病去世,而一个月前我还在翻看他的非洲游记。一幕一幕,在黑暗中变得无比鲜活起来。
我靠着一棵树站住,闭上眼睛,努力始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候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我当然没有准备好去承受失温、极度疲劳、滑坠以及随之带来的伤害以及死亡!人,生而不自由,是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从出生到坟墓都与周围的人相互羁绊。
当医疗车从91km处折返,我终于开口求助。
“怎么了?”
“冷!”我的语言系统仿佛冻僵了,只能挤出这么一个字。体温表显示外耳道温度只有34.4,如果说疼痛只是主观感受,那么生命体征便是切实存在的 “red flag”,提示不能再继续了。多年以前在雪山上,见过距离顶峰只有100米之遥的登山者因为高反下撤,现在终于尝到了那份苦涩。
我被运送回CP5。系统测量生命体征,血压也已经降至88/60。一个坐轮椅的女医师建议我立刻躺下避免晕倒,并裹在睡袋里喝热茶回温,每10分钟测一次体温,不能自行回温只能送去医院进一步治疗。我这才注意到墙边已经躺了一整排失温的选手。
人其实就是这么渺小脆弱的动物-温度、酸碱度、氧气…维系生存的要素必须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否则就会崩溃,会死;人却也是太坚韧和强大的动物,当第二天听到小明近26小时最终完赛的时候,我深深这么觉得。
可以明确的是:我怕死!很怕!
半个小时之后,老公从终点赶回CP5。签署退赛声明,自始至终,居然维持着异常的平静,没有哭。
努力至今,还剩下最后11km,我失败了吗?没有!只是未完成!很难说什么样的选择是最佳的,但至少这个选择是基于我的自由意志作出的
回到旅店,天光已渐明。终于在清晨受到小明的短信,只有四个数字:
“25:40”

2017 澳大利亚The North Face 100 Blue Mountains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不同见解,原创频道欢迎您来分享。来源:爱燃烧 — http://iranshao.com/diaries/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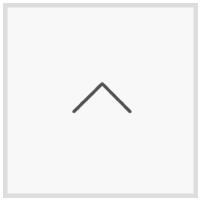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